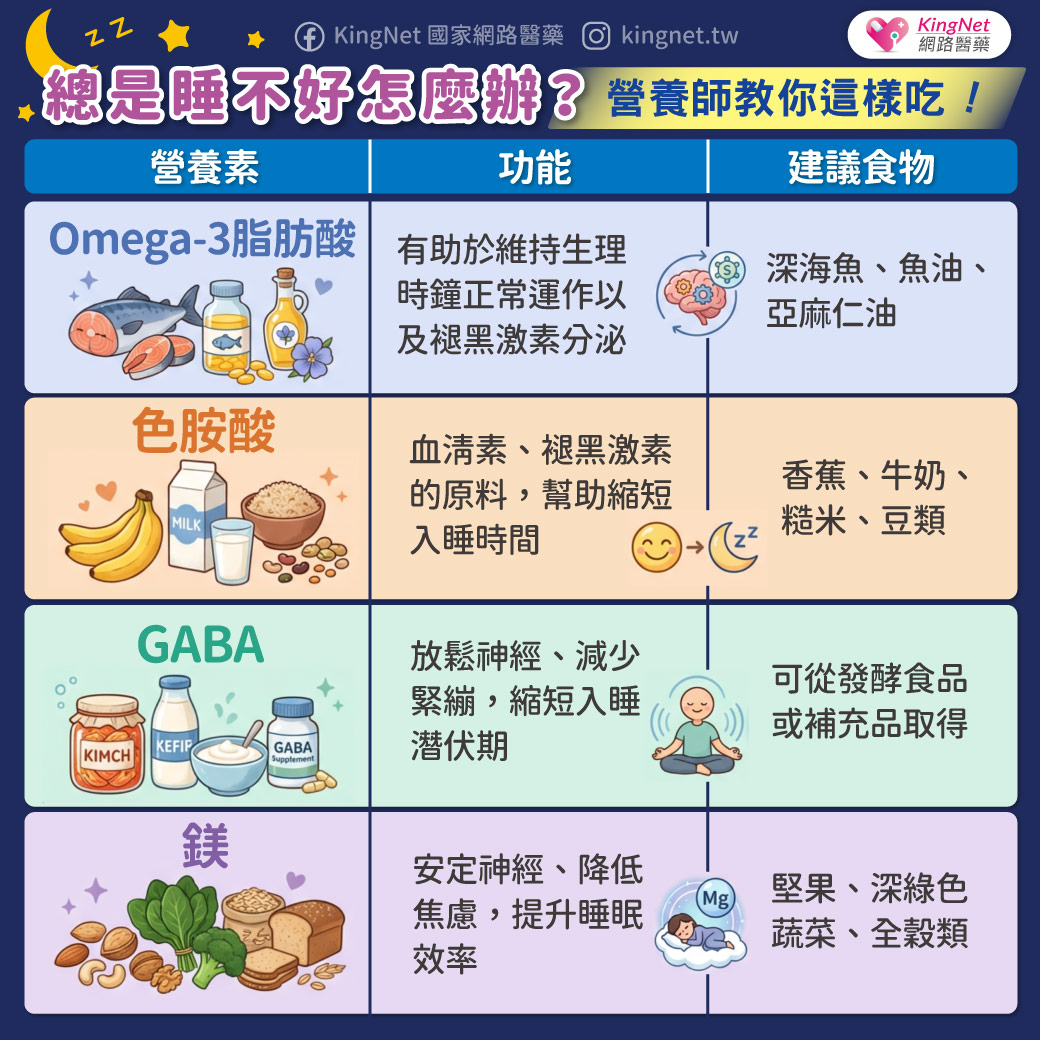文:新光醫院精神科 主治醫師 陳俊光
門診室中,一對夫妻正在互相指責,指責對方該為婚姻中的衝突負責,對方才是病人,才是該看精神科的人。
看著他們,我彷彿回到宗教改革時的歐洲:新教徒與舊教徒間用紙筆或用刀劍互相攻擊,指責對方是異端、是魔鬼附身,得勝的一方就把對方送上火刑臺,把異己者燒成灰,也暫時燒掉了自己的恐懼──被人群排斥、被燒成灰燼的恐懼。而精神科就是現代的宗教裁判所,醫師是宗教裁判官,病房就是火刑臺。
人們害怕精神科,因為他們害怕被判生病像怕被判有罪,他們怕被人群排斥就像怕被監禁隔離;而許多人面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態度也就像面對罪犯或異教徒,排斥、拒絕、漠視、甚或剝奪其基本權利,也無怪乎這麼多人視精神科就醫為畏途了。
然而,精神疾病患者和其他人(所謂“正常人”)真有那麼大的差別嗎?
我們指稱一個人是否為精神病人之準繩乃是:這個人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這時代所認可的行為模式。
──荷妮 焦慮的現代人
Karen Horney :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
荷妮指出:我們對正常的概念,乃是根據某一團體加諸其成員的行為和感覺標準而定的。然而事實上,這些標準會隨不同文化、時代、階級和性別而有差異。封建貴族們會認為:男人整日游手好閒、只在打獵或作戰時才活動是十分自然的;而小資產階級如果表現出這種行為態度,則會被認為精神不正常。現代精神醫學常以幻覺作為疾病診斷依據;但是在印地安人中,對幻象的體驗乃是精靈所賜予的無上榮耀,是天賦異稟的證明。在一百多年前的歐洲,手淫、口交或婚前性行為被認為是不正常的;時至今日,還有這種想法的人反而會被認為是怪異的。
許多的學者曾探究瘋狂的觀念及其起源,其中尤以傅柯(Michel Foucault)為代表。廣被接受的看法認為:瘋狂的概念與中世紀的女巫審判和痲瘋病院有關;當時有不少行為異於習俗者被當作女巫燒死,隔離脫軌者的作法則源自隔離痲瘋病的概念和社會經濟需要,而女巫與痲瘋病患均被視為魔鬼附身,是邪惡的罪人與不潔淨者。
一直到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代,科學的概念才逐漸取代了原來的神學概念。從那時候起,瘋人不再被視為魔鬼附身的罪人,而是像一些會傷害他人或沒有生產力的人;不變的是,他們仍然被視為不潔淨的,他們仍然被排斥、隔離,如同罪犯、酒鬼、淫行者,以及乞丐、窮人等不能適應社會生活的人。
紐約大學精神病學教授薩斯指出:現代精神病學的意識型態,僅是傳統基督教意識型態在科學時代的變形而已。
人不再生來就是罪人,而變成生來就是病人。
而引導(控制)這些罪人(病人)的責任(權力),也由神父轉交到醫師的手中。
事實上,近數十年來,精神醫學界已逐漸變得較為謙虛而能反省:自知所謂的異常狀態必須考慮社會文化因素,自然有其主觀的侷限性。
因此,所有精神疾病的診斷準則均包含這一條件:“此狀況已造成當事人本身的困擾或是社會功能的損害”;雖然仍保留社會功能(適應)的字眼,但至少願意考慮當事人的感受並將其置於前面,較諸過去數百年的精神病學觀念,顯然是重大的進步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:一九七三年在美國精神科學會中,醫師們終於正式將同性戀排除在精神疾病之外。
既然如此,何以精神疾病還是這麼令人懼怕,這麼被排斥呢?
人們不能藉著禁閉自己的鄰人來確認自己神志健全。
──杜思妥也夫思基 作家日記
Dostoievsky : Diary of a Writer
一個智能不足者每天耗費國家三點五馬克,精神病患則是每天四馬克,癲癇患者則耗費每天四點五馬克,以上三種人平均每天花費國家四馬克;他們占德國人口約二十萬人。如果他們全部消失,國家一年可以省下多少錢?
──電影“美麗人生”
(Beautiful Life)
就像人們需要偶像崇拜,人們也需要有共同的敵人,他們藉此確認彼此的共通性,確認他們是屬於同一個團體的;而藉著施加於這共同敵人身上的暴力懲罰,他們更可以彼此嚇阻,嚇阻他人不觸犯這個團體的禁忌;藉著這共同敵人的鮮血,人們也自覺獲得淨化與救贖。
而這幾乎是社會學的定律,即:社會規範的要求與真實的人們行為之間落差愈大時,就愈需要犧牲一些代罪羔羊,以便維持人們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神話,以及人們公開主張的倫理觀念。
舊約聖經利未記有一篇記載可作為最古老而貼切的說明:
“亞倫兩手按在活公羊的頭上,承認以色列人諸般的罪孽與過錯;並將他們一切的罪愆都歸在公羊的頭上,藉著受委託者的手送到曠野去。要把這隻羊放在曠野,這隻羊要承擔他們(以色列人)一切的罪孽,並帶到無人之地。”
精神病人就是這個時代的羔羊。人們用瘋人代表負面,透過對比,凸顯社會或個人那虛構的正常性。
於是,從基督徒殉教者開始,到女巫審判、到異教徒,到猶太人、吉普賽人、黑人、「黃禍」,到同性戀者、政治上的異議分子,這形形色色的人對人的迫害,都是代罪羔羊的獻祭。社會把恐懼與矛盾轉移並固定在一種虛構的形象上,其他的矛盾得以(暫時)消解,社會和個人得以(假象地)淨化。
瘋狂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成為重要的象徵與代罪羔羊。起初癲狂者被驅逐出眾人居住的城市,有的被送上愚人船,終其一生在各城市間的河川上漂流。其後他們被送到教會或政府設立的大型療養院中,冷月孤窗(甚至腳鐐手銬)伴其餘年。在納粹時代的德國,他們與猶太人、共產黨(另兩種代罪羔羊)一同被送入毒氣室,為的是“潔淨日爾曼民族的血液”、同時“節省國家資源以供戰爭所需”。
而最離奇的是:史達林時代的蘇聯,經常將政治異議者當作精神病患,並將之隔離監禁,這又是利用精神病學作為社會控制手段的實例。
然而,精神醫學界也不缺乏勇於反省改革的先驅。皮內爾(Pinel)在十九世紀初即致力於解放精神病人;一九六零年代美國的去機構化運動(deinstitution- alization)也讓許多病患得以重返社會。當然以更前進的觀點檢視這兩個行動,仍可發現其中混有些偏見,執行的過程中也有許多問題發生;但比起過去數百年來的壓迫,這樣的努力實在是值得讚美的。甚至在納粹高壓統治下的德國,也有不少精神科醫師不顧個人前途,願意犧牲自己的權益(甚至生命與自由),反抗希特勒的精神病淨化政策。
人類必然瘋狂,而不瘋狂也意謂著另一種形式的瘋狂。
──巴斯卡(Blaise Pascal)沉思錄 卷六 思想的尊嚴
根據一般的統計,歐美大約五分之一的人一生中至少有過一次以上的憂鬱症(各種型式的)發作,患有(某一種)焦慮性疾患的更高達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;即便是被視為較嚴重而少見的精神分裂症或躁鬱症,也各占一般人口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,臺灣應該相距不遠。這麼常見的疾病、這麼多的患者,為何周圍卻少有人(願意被別人知道)曾至精神科就診,少有人自認有這方面的困擾呢?是否他們害怕承受過去歷史上女巫、異教徒、乃至痲瘋病患者的相同命運,害怕被排斥、被剝奪作為社會人的權利呢?
的確,目前社會上仍充斥著對精神疾病(以及各種差異狀態)的偏見與歧視。周圍人們怪異的眼光、工作上的限制、各種私人保險的不公平對待、甚至曾有人主張精神病患不得搭乘捷運;而一旦被視為精神病患,往往其言說就被視為無意義的聲音(如同異教徒、吉普賽人、政治異議分子、弱勢者等沒有聲音的人)。難怪人們害怕被當成病患,而且會在有激烈爭執時努力把對方定義為精神病患──就像那對在診間吵架的夫妻。值得警惕的是,人們在逃避精神疾病(或同性戀、……)污名的同時,是不是也更加強了這污名化、這歧視與迫害的嚴重性呢?
值得慶幸的是,越來越多精神醫療(及各種助人專業)人員對個案具有善意且尊重的──當然,以更前進的標準而言仍有不足。專業人員願意把個案視為完整的人,在大部分的狀況下有完整的人權;願意維護個案的隱私,也願意協助個案爭取應有的權益。更重要的是,愈來愈多的專業人員開始學習:不再把個案視為“病人”,不再用疾病看待個案的一切;畢竟,求助者不一定是“病人”,他們是“受苦的人”。
我們希望:有困擾的人的人能勇於向專業人員求助,無論是生活作習上、情緒處理上、或是人際關係上的困擾,或是其他科醫師或親友建議尋求協助的狀況,一般專業人員都會在尊重個案的前提下盡力協助處理。也希望我們的社會能更尊重這些受苦的人、尊重各種差異狀態,不再以瘋狂或疾病之名行歧視迫害之實。
作者簡介:
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
台灣向日葵全人發展協會附設向日葵工作室心理治療專業人員
KingNet國家網路醫院 一般門診 精神科線上諮詢醫師